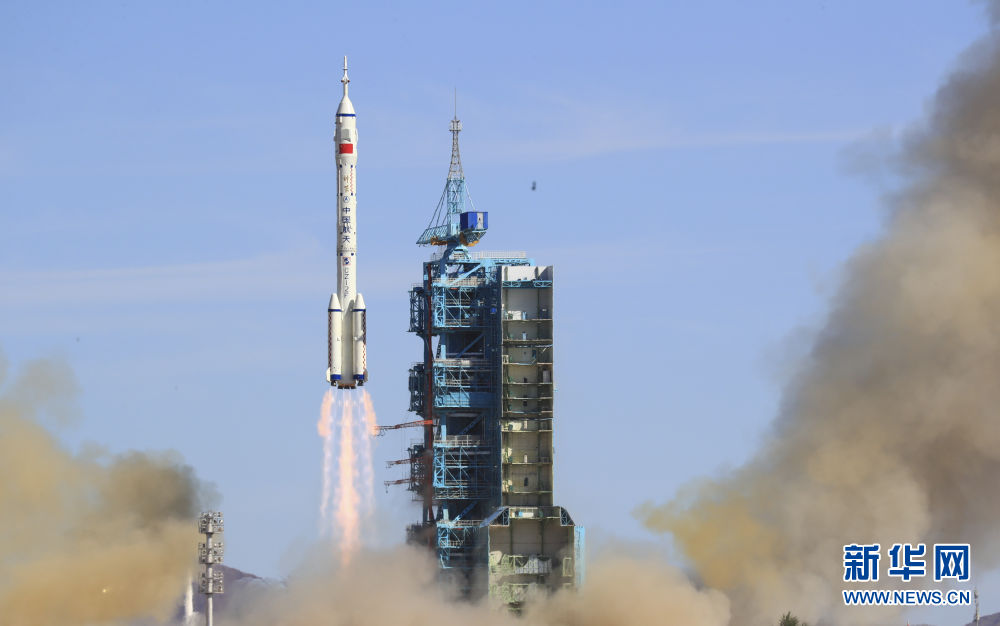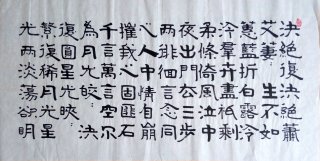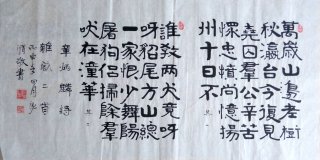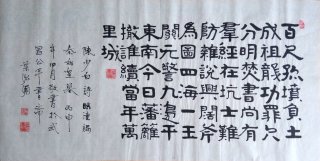“八百壮士”的悲壮传奇(2)
辛亥革命网 2015-07-24 10:56 来源:张汇滔研究 作者:田际钿 查看:
困居孤军营:等待时机重返前线继续抗日
我们幸存的500多名官兵进入租界,在跑马厅休整了两天,租界工部局派了13辆卡车载着我们开往孤军营,战士们虽然个个衣衫褴褛,但英姿焕发,站在汽车上沿途受到市民们的热烈欢呼。卡车开进军营,工部局派了三四十名白俄士兵驻孤军营担任警戒,营内四周安装了铁丝网,只准官兵在营内活动,不准外出,不准与外界接触,实际上是失去了人身自由,过着囚禁生活。
开始3个多月,饭菜都是由英国人请人做好后送到营内,早晨稀饭,中午、晚上吃米饭加一点儿萝卜、黄豆。因饭菜做得不好吃,又不卫生,孤军营便向英国人交涉,根据有关协议,将定量供给的钱米直接给营部,由我们自己打灶做饭,得到同意。孤军营人才济济,泥瓦匠、缝纫工、做皮鞋等各方面人才应有尽有。官兵们很快用芦苇搭起了草楼,生产鞋子、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除自用外,部分销到上海、四川和新加坡等地,弥补了生活费的不足。我被安排当织袜工,那期间还学习了两年文化。
在困居孤军营的日子里,谢晋元一再叮嘱我们要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等待时机,重返前线,继续抗日,把侵略者赶出国土。但是,租界工部局迫于日本人的淫威,多次阻止我们正当的爱国活动,日伪特务机关千方百计想瓦解孤军营,不断地使用各种伎俩进行破坏。孤军营每天要举行升旗典礼,全体官兵集合在国旗下,立正敬礼,高唱国歌,让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孤军营上空高高飘扬,同时列队向前方牺牲的将士默哀。1938年8月的一天,我们正在升旗,工部局派来大批“洋兵”把营地团团包围,四周站岗的白俄士兵冲进操场抢国旗、砍旗杆。为了保护庄严的国旗,全营官兵在谢晋元的指挥下,用砖头、酒瓶,菜刀、铁叉作武器与白俄士兵展开了肉搏战,“洋兵”见状急忙冲进操场用警棍、水龙头对孤军官兵猛袭,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战士2人,打伤300多人,白俄巡警被打死了两个。傍晚,工部局封锁了孤军营,用卡车将我们押往外滩中央银行囚禁。事后,孤军营官兵绝食3天以示抗议。由于上海各界人士的声援和我们激烈的抗争,工部局不得不释放我们,解除对孤军营的封锁,并允许孤军营每逢节日、纪念日升旗,但旗杆截去了一节。孤军营的活动,引起了日军和汪伪汉奸走狗们的忌恨。他们千方百计想收买孤军营,多次拉拢谢晋元团长,都遭斥责。有一次,日本佬发放一些表格,给我们每人一张,要我们填写志愿参加“和平军”,不少战士在表上写“我要回家”,有的战士写“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当和平军”。我当时填的是“宁死不当亡国奴”。
日伪的诱降活动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便恼羞成怒,萌生杀机,从孤军营内部买通以郝精诚为首的一伙败类暗杀了谢晋元等人。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国民政府追认谢晋元为陆军少将。孤军营还为谢晋元铸造了铜质纪念章,发给官兵佩戴,音乐家们创作了《谢晋元团长追悼歌》,当时在社会上广为流唱。
谢晋元遇难后,雷雄代理团长,与团副上官志标一起领导孤军营官兵继续与日伪进行斗争,直至1941年底孤军营解散。
流放荒岛:宁死不当亡国奴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孤军营地也落入敌手。日军将我们作为战俘抓起来,先送到上海宝山县一个集中营关了一个半月,后又押往郊区的龙华县。当时,龙华至宁波有条铁路,为了堵住附近地区的老百姓,不让他们靠近孤军营,日军决定在离铁路外10米处挖一条深坑,长2000米,宽深各三四米。每天天不亮,日军就强迫我们起床,前去挖坑。深坑挖到两三米就有水,泥泞不堪,稍一怠慢就要遭到日军士兵的鞭抽毒打,午饭就在工地上吃些豆腐渣之类粗劣的饭食。
孤军营的行踪一直为世人关注。一天,有个日本士兵在工地上发现了一封埋着的信,内容是告诉孤军营的官兵,新四军在打听我们的下落,准备营救。原来,孤军营里有个清洁工就是新四军通过上海租界工部局打进来的。日军获悉此信后,大为震惊,急忙给孤军营官兵们分发饼干、面包等食品,要我们收拾行李马上转移。随后,我们被送往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不久,12名士兵越狱逃跑,但跑到南京中华门时被日军抓住,日军当即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残忍地刺死。
1942年秋,日军将孤军营一分为二:一部分押往浙江裕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筑路做苦工,另一部分送到西南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服苦役。那天,连我在内一共36人被押上了日军的一艘大型军舰。因为怕中国和盟军的飞机轰炸,一般晚上航行,白天停靠码头。军舰共9层,我们被赶到最底层,不见天日,里面热得出奇,没有床,不少人晕船、拉肚子,有一个来自通城县的湖北老乡就热死在舰上。军舰在太平洋上共漂泊了48个昼夜,到达澳洲一个叫新不列颠岛的荒岛上。这个岛位于西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湾之间,四周都是10米高的树,荒无人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被日本海军占领,日军在岛上建了许多补给仓库。
上岛后,“孤军营”的人被拆散,我们12人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队里共有160名战俘,其中包括新四军、游击队战士。在岛上一起服苦役的,还有英国、美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战俘。在“勤劳队”服苦役的日子里,我们简直是过着非人生活,劳动十分繁重,生活极其艰苦。一天要进行十多个小时的繁重劳动,住的是岩洞,瓜薯当餐,有时还吃日本人丢下的猪牛内脏和骨头。没有医疗条件,如果患病搞不好就眼睁睁等死,经常看到残忍的日本兵把死亡和重病的战俘用卡车运到深山里去埋掉。当初160人的中国劳工队,两年多后只剩下38人。我的3位蒲圻老乡向寿山、雷炳林、刘炳杖,连累带病,于1943年前后死在岛上。我与难友含着眼泪,秘密地掩埋了他们的尸体,日本投降后又把尸体移入国际公墓安葬。
日军经常欺侮中国士兵。一次,有个块头较大的日军上士,看到我身体较瘦弱,便上前叫板:“咱们摔跤你赢了,这条烟给你米西米西;我赢了,打你两个耳光。大大的,好不好?”我本不想理他,但看到对方气焰嚣张,着实想教训他一番,就点头同意。日本佬猛扑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我就趁势弯腰将手伸向对方档部,用力一扳,将鬼子兵重重摔倒地上。旁边的中国难友都向我投以钦佩的目光。
1945年8月,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了。不久,麦克阿瑟统率的盟军澳大利亚13师乘舰驶近该岛海岸。岛上的中国战俘获知后欢呼雀跃,我们二三十人下海一直游了500多米后爬到舰上,和上面的盟军士兵一齐享受胜利的喜悦。
1946年12月底,我们31人被国际红十字会遣送回国。我们经香港回到上海,上海市政府组织人到港口迎接。在上海住了一些时候,国民政府对我们这些在抗日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态度逐渐冷漠,既不安排工作,也没有什么优待。这时我感觉国民政府当时对八百壮士鼓噪一时的宣扬不过是为粉饰国民党坚决抗日的门面而已,从此心灰意冷。不多久,国民党当局又以升官为诱饵,诱使我们上东北战场参加内战,但我们好些人抱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念头,坚决要求解甲归田,经过斗争终于得以成行。上海市政府也就顺水推舟给了我们一些路费。我孤身一人,回到了阔别几十载的家乡鄂南烟墩。